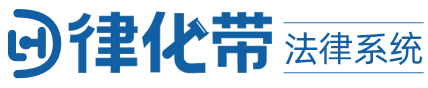刮码剪码刮标剪标的商标或不正当竞争理论与实务及反刮码及诉讼建议
【附15省市是否侵权案例裁判要旨】
作者:浙江杭知桥律师事务所 王梨华 周靖超
【导读】
第一部分:刮码剪码刮标剪标的商标或不正当竞争理论与实务及反刮码及诉讼建议
第二部分:15省市是否侵权案例的裁判要旨
目录
第一部分、刮码剪码刮标剪标的商标或不正当竞争理论与实务及反刮码及诉讼建议
一、刮标刮码类型
(一)明码与暗码
(二)商标码和非商标码
二、法院对不同类型的刮码行为界定不同
(一)法院对“非商标码”的刮码行为界定不同——部分举例
(二)法院对“防伪码”的刮码行为界定不同——部分举例
(三)法院对“商标码”的刮码行为界定基本相同
三、 保护商品—保护标识—商标禁用权本质三阶梯递进
(一)从保护商品至保护标识的转变
(二)从保护标商标至关注商标禁用权本质的转变
四、我的“商标地盘”我做主与“非必要不破坏”原则
五、弃标构成商标侵权
六、 防伪码刮除是否可以免除原告证明假货的责任
(一)证明真假为原告天然责任
(二)证明真假为原告天然责任的例外
七、权利用尽原则豁免刮码的例外——“货标分离”
八、剪标、弃标、剪码、弃码的归责
九、反刮码的实务建议
(一)明码与暗码组合使用
(二)多使用商标码
(三)提示刮码商品为非可靠商品
(四)经销商的刮码的违约责任
十、 诉讼选择
(一)在哪里诉最关键
(二)刮防伪码性质更严重
(三)是否告知消费者是一个重要因素
(四)从原告角度而言既主张商标侵权又主张不正当竞争
(五)刮码行为的实施主体
第一部分 刮码剪码刮标剪标的商标或不正当竞争理论与实务及反刮码建议
【关键词】:刮标、剪标、刮码、剪码、弃码、反刮码、非必要不破坏、商标侵权、不正当竞争
前言
识别商品或服务来源是商标首要功能,消费者通过依附于商品(或包装)的标识建立起其与商品或服务之间对应联系。
近来品牌方出于防伪、溯源、渠道管控、价格管控、流通管控(防串货)、大数据流调等多维度需求,在商品或包装上设置识别码(通常为条形码或二维码),但一些经销商往往出于防溯源和反管控的“经营策略”,将识别码进行刮除(称为“刮码”)或剪去部分(称为“剪码”),甚至将整个识别码丢弃(称为“弃码”,有的是通过不发外盒或丢掉半个盒子实现),本文从商标侵权或不正当竞争两个角度讨论。
一、刮标刮码类型
(一)明码与暗码
1.明码
明码是指品牌方将识别码(比如条形码、二维码、RFID射频、渠道码、防伪码)设置成肉眼可见,消费者和品牌方可扫描出信息,可根据不同扫码设备或身份或权限请求反馈得到不同内容或不同详细程度信息,如消费者扫码反馈的仅为真伪信息,而品牌方扫码反馈包括真伪外,还包括渠道、流通环节、价格等诸多信息。
2.暗码
暗码是指品牌方将识别码设置成肉眼不可见,只有通过特殊设备且知道暗码的设置才能准确扫码反馈出具体信息,暗码好处一方面可以不呈现大面积的识别码而影响美观;另一方面部分经销商不知道暗码位置,可以更好隐蔽性。目前一些品牌方将暗码设置在公司名称、商标、产品配方、产地、生产日期、保质期等对于商品信息特别重要的区域位置上,一旦渠道商刮暗码对商品比较重要的信息丢失。
(二)商标码和非商标码
1.商标码
商标码是指将识别码的位置设置在商标上,即识别码的底纹有商标标识,如果刮了识别码势必会刮掉商标,会对商标标识进行了破坏。
2.非商标码
非商标码是指,类似传统的识别码只是设置在如包装盒的空白位置或其他非商标标识位置。
二、法院对不同类型的刮码行为界定不同
(一)法院对“非商标码”的刮码行为界定不同——部分举例
1.玫琳凯公司诉马顺仙案
该案件为二两终审案件,二审法院与一审法院的观点相反,二审法院将是否告知消费者刮码详情作为考量是否构成侵权的因素之一。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未经商标权人许可隐匿、刮损、篡改商品上附载的重要信息,破坏商品的完整性,使公众建立起错误联系,割裂了商品与商标权人的特定联系,破坏了注册商标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被告的刮码行为使原告无法跟踪产品质量,破坏其用户粘性,原告对其商品的渠道无从追溯,妨碍了其正常经营,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
二审法院认为,被诉产品系正品,根据商标权权利用尽原则,商品在被第一次投放到市场后,权利人即丧失控制权。同时,被告在网购页面中对刮码原因进行解释,未损害消费者的知情权,实现消费者福利最大化,不构成商标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
2.完美(中国)诉绍兴市柯桥区杨汛桥镇胡素娟保健品店案
法院认为,虽然商品的生产批号部分及二维码部分被刮除,但该种改变所导致的差异性和该种信息的缺失,并未达到影响商标指示商品来源功能的程度,涉案刮码行为不会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不构成商标侵权。但是,被告销售刮码商品的行为,攫取了其他合法经营者的交易机会,破坏了经销该品牌商品的所有经销商之间的正当竞争秩序,构成不正当竞争。
3.浮美实业(上海)有限公司诉王雄案
被告以刮码销售的不当方式出售被诉侵权产品,但未实质性改变被诉侵权商品的外观、品质,也未破坏商品的商标标识,虽然刮除了部分溯源码,但并未达到影响指示商品,不构成商标侵权。(笔者注:事实上因为刮了暗码是破坏了设置在暗码上的商标的),笔者认为,浮美实业(上海)有限公司诉王雄案中,通过侵权比对能明显判断出被告的商品刮除了一处瓶身中心位置且范围较大的主要商标,但法院判决中认为“未破坏商品的商标标识”,另外可能受“玫琳凯案件”的影响。但是,由于原告具有案件之外的其他因素的综合考虑,本案未提起上诉。
(二)法院对“防伪码”的刮码行为界定不同——部分举例
1.东莞市益科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诉云龙区梦梦羽毛百货商行、孟佩案
该案件为二两终审案件,二审法院与一审法院的观点相反,二审法院将商标标识本身的完整性作为考量是否构成侵权的因素之一。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在销售原告生产的商品时,将产品上的防伪查询码撕掉,割裂了商标与商品间的对应关系,破坏了上述商标所具有的品质保障功能,构成商标侵权。
二审法院认为,被告将正品标识码损坏后进行出售的,如果被控侵权产品与正品一致,亦明确标有正品商标、产品名称、生产厂商等来源信息,撕码仅使得产品的标识码不完整,缺失查询功能,而并未破坏商品本身的商标标识,亦未使得产品的品质统一性受到破坏,则该撕码销售行为并未妨碍商标识别功能与品质保障功能的发挥,不构成商标侵权。
2.某某公司诉周某案
法院认为,涉案商品防伪码被刮除,无法直接进行防伪验证,不能证明涉案商品系正品。因此,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的,以及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均属于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
(三)法院对“商标码”的刮码行为界定基本相同
裁判结果为构成商标侵权。裁判思路为:刮码而导致无法确定为正品。即便被告提供了合法来源,但是破坏了商标的完整性,割裂了消费者与标识之间的联系,构成商标侵权。例如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多处被刮去商标、防伪码、商品二维码、商品信息标识,导致公众容易产生混淆和误认。
三、保护商品—保护标识—商标禁用权本质三阶梯递进
(一)从保护商品至保护标识的转变
商标侵权主要围绕“商品”和“标识”两个角度,传统商标侵权理论或实践往往讨论商品本身真假和商品品质,但随着像“南极人”这种“卖吊牌”(就是“卖标”)经营模式的出现,商品只有配搭商标权人售出的吊牌才是正品,是否侵权关注的不再商品本身,而在于“吊牌”的真假,如果吊牌是假的即使商品品质再高也仍然是“假货”,考量更多的是商标标识的真假,注意力从保护商品真伪转为保护标识真伪。
(二)从保护标商标至关注商标禁用权的转变
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本质上是否获得商标权的人的许可是关键。例如,超过商标权人许可贴牌加工出来的商品,即使“商品”和“标识”与正品完全相同或者比正品品质更高,也难逃商标侵权的命运,本质上不再需要与正品进行真假货对比,推定为商标法意义上的假货。再例如将正品不合理的“散装”或“分装”销售也往往构成商标侵权,因为未获得授权是侵权的核心本质,所以注意力又从保护标识到关注禁用权的转变。
四、我的“商标地盘”我做主与“非必要不破坏”原则
从保护商品到保护标识到本质的禁用权的转变,强调了“标识”的重要性,标识既包括基本识别功能,标识还包括其特有的文化风格功能,从鼓励创新,鼓励独立发展各自品牌的立法本意出发,标识除了基本识别功能,更鼓励从风格角度创新自己的特有标识风格,与其他商标权进行更有效的差异分离,进一步加强商标的识别功能,符合商标法区分各市场主体,避免混淆的立法本意。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标识是一个商品的灵魂和最高荣誉,甚至超过商品品质本身,商品品质是商品的外在表现和载体,而标识却是商品品质的升华和结晶,标识代表权利人的文化,赋予其文化和法律两个属性,形象地说我的商标地盘我做主,要充分尊重商标权人的自主的商标文化观。鼓励和保护商标权人参照民法自治角度对自己商标的特有或自主的展示方式。
一旦商标权人选择了其特定的标识,其他市场主体应充分尊重商标权人。笔者首次提出“非必要不破坏”原则,即未经商标权人许可,除非行政监管或公共利益等原因和必要以外,不得随意破坏商标权商标标识,例如使用不同的颜色、大小、字体、排列方式、组合方式,标识位置,以及尊重是否使用商标,使用几个商标,不能破坏标识的完整性,使用与商标权人表现形式不一致的标识。类似版权中的作者署名权,是否署名,署真名还是笔名,署名的书法字体等都是作者的自由选择且应当保护的权利,与保护作品完整权的概念相当。
笔者认为刮“商标码”破坏了商标权人的自主的商标文化观,割裂了商标与权利人之间的特有联系,构成商标侵权。退一万步讲,如果商标侵权构成有困难,也可以从反不正当竞争第二条的诚实信用条款出发,构成不正当竞争。
五、弃标构成商标侵权
商业实践中,一件产品同时使用多个标识,如一货二标的情形十分常见。尤其拥有较高知名度品牌,其商品包装装潢之状态也会成为消费者识别所延及的重要依据。商品本身的标志与商品包装装潢的标志共同影响了消费者的判断,而对于任一标识的减少都可能削弱商标的识别来源功能,笔者认为弃标构成商标侵权。
再如,“南极人”品牌“卖标”商业模式,商标权人根据标识(比如吊牌)数量收费,存在一件商品配置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数量标识才构成一套最低计费单元卖标的情形,如果买标的经销商(商标被许可人)销售时在商品上不放置标识或少放置标识,则应当认为未放置标识或少数量放置标识的商品为侵权商品,笔者认为属于构成商标侵权。
但如果丢弃的是部分标识,总体上商标识别功能未被破坏,产品本身是正品,法院往往可能不以商标侵权论处。
六、防伪码刮除是否可以免除原告证明假货的责任
(一)证明真假为原告天然责任
商标侵权案件,一般来说证明假货是原告天然责任,不以被告未获得授权,不以被告未提供合法来源而被豁免。但如果刮掉“防伪码”能否直接推定假货不能一概而论。
(二)证明真假为原告天然责任的例外
如果该商品唯一(或者通过其他办法已经非常困难)通过“防伪码”来区分真伪,我们认为原告已经举证责任完成,此时举证责任转移到被告身上,被告未提出合理且充足理由或证据(提供了进货来源哪怕是商标权人处的直接来源也未必认为是充足证据),则可以推定是假货,但在刑事案件由于证据要求超出民事证据的“高度盖然性”要求则这种推定可能还不够。
按郑州中院的观点,通过大面的破坏商品包装完整性,导致公众无法通过确认相关信息在商品与商标权人之间建立起特定联系,从而无法准确获得完整无误的商品来源信息,容易产生混淆和误认,此时应推定为假货,由被告举证。
从物理形态上来说,刮码导致原告无法辨别是否为假货,很难证明被控产品的真伪,推定为商标法意义上的假货,即证明责任从原告转移至被告,或者引用郑州中院法官的观点,由于刮码使得无法判断被控产品是否与正品一致这种表达,潜台词为假货。
有观点认为,因涉案商品防伪码被刮除,无法直接进行防伪验证,而被告不能证明涉案商品系正品,推定为假货。
有观点认为,将产品上的防伪查询码撕掉,割裂了公众通过上述注册商标与商品间的对应关系,容易产生混淆和误认,构成商标侵权。
七、权利用尽原则豁免刮码的例外——“货标分离”
权利用尽也有例外,商标法的“反向假冒”就权利用尽法定的例外,换标后即便货本身是正品仍然构成侵权,剥夺了商标在市场上展示的机会。
换言之,权利用尽原则的试用不能破坏或削弱商标识别商品或服务来源的基本功能。权利用尽主要是解决流通环节的顺畅,且是在不破坏原物原标的情况下,即商品(含标识)未改变的情况下可以在市场上畅行无阻,因为这样仍然保持着商品的“原汁原味”,如果一旦改变商品的“原汁原味”的原貌,通常在物权的角度来讲没有太多问题。但即使行使物权的时候叠加物权的其他权利,比在《著作权法》中,美术等作品原件所有权的转移,不视为作品著作权的转移(展览权除外)。
商品的品质(包括标识的品质)被改变,无论是提升商品品质抑或粗制滥造,“一货”与“一标”或者“货标不分离”的特定对应关系不应该被打破,这是保证商标识别来源功能,维护商标秩序稳定的需要。二维码刮除行为无疑削弱了商标来源识别功能,二者之间的联系被削弱甚至破坏割裂时,权利用尽原则在该种情况下能否适用,应当慎之又慎。商标权的本质是一种禁用权,商标权人依法享有禁止他人未经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众多商标侵权行与对于商标权性质的误解离不开。即便侵权人行为未对商标权人声誉等造成损害,但未经允许擅自使用他人注册商标行为本身,已经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
八、剪标、弃标、剪码、弃码的归责
剪标是直接破坏商标,可以按商标侵权来归责。弃标笔者认为破坏商标的使用方式的完整性,如果是涉及假货类的(刮防伪码)可以按商标侵权规制,或者在卖标的业态下少标就是未经许可行为,可以按商标侵权来归责。剪码(非商标码)和弃码(非商标码)是破坏商品完整性的不诚信行为,主要按不正当竞争来归责,如果正品刮码(刮的不是商标码)通常按不正当竞争规制,至于是否能规制成功,各地法院观点不一样而已。
九、反刮码的实务建议
(一)明码与暗码组合使用
明码可以方便消费者扫码,而暗码可以方便权利人查控,更进一步讲还将暗码设置在公司名称、产品配方、产地、生产日期、保质期等对于商品信息特别重要的区域位置上,细节上让刮码者刮掉年份的最后一位数字,而不是月份,年份更重要。一旦渠道商刮暗码对商标比较重要的信息丢失,对于消费者更不易购买,同时更容易构成商标侵权或不正当竞争。
(二)多使用商标码
可以将明码或暗码设置在商标标识上,提高被判定为商标侵权或不正当竞争的几率,对于刮码者造成更大的威慑力。给品牌方有用的实务建议包装上所有区域全部设置暗码,那么要刮的话就会刮的面目全非,此种情况,法院再认定为正品从而不构成商标侵权不正当竞争的可能性,笔者认为就很小了。
(三)提示刮码商品为非可靠商品
在商品或包装上提示,如果刮码的商品为非可靠商品,不提供售后服务等消费风险提示。
(四)经销商的刮码的违约责任
与经销商签订经销合同中约定若经销商刮码销售的承担违约责任,通过合同约束经销商。
十、诉讼选择
(一)在哪里诉最关键
目前关于刮码的裁判规则像极了“诸侯割据”的状态,同样的事实,不同法院给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观点,因此选择管辖法院成了重中之重。
(二)刮防伪码性质更严重
防伪码涉及真假货问题,如果被告无法证明来源或者有其他因素,则很容易推定为假货,此类可以往商标侵权靠。
(三)是否告知消费者是一个重要因素
被告是否将刮码情况告知消费者成了很多法院裁量是否侵权的重要考量因素。
(四)从原告角度而言既主张商标侵权又主张不正当竞争
不同法院对两个案由有不同认知,为保险起见,同时主张双案由,保底不正当竞争。
(五)实施刮码行为的主体与销售刮码产品的主体
被告是刮码行为的实施主体还是刮码产品的销售者,刮码产品的销售者是否可以主张合法来源抗辩,取证时可以通过聊天记录方式予以确定。如果网页上有说明,至少可以认为被告知道产品为刮码产品,因为网页的编辑行为是经销商完成的。
第二部分 15省市刮码案件裁判要旨
目录
第二部分、15省市刮码案件裁判要旨
一、浙江省刮码案件
(一)不构成商标侵权、不构成不正当竞争案件情况
(二) 不构成商标侵权、构成不正当竞争案件情况
二、上海市刮码案件
(一)不构成商标侵权、不构成不正当竞争
(二)构成商标侵权
三、江苏省刮码案件
(一)不构成商标侵权
(二)构成商标侵权
四、河北省刮码案件
(一)不构成商标侵权、不构成不正当竞争
五、安徽省刮码案件
(一)不构成商标侵权、构成不正当竞争
六、福建省刮码案件
(一)不构成商标侵权、构成不正当竞争
七、江西省刮码案件
(一)不构成商标权侵权、构成不正当竞争
八、山东省刮码案件
(一)不构成商标侵权、不构成不正当竞争
(二)不构成商标侵权、构成不正当竞争
九、河南省刮码案件
(一)不构成商标侵权、不构成不正当竞争
(二)不构成商标侵权、构成不正当竞争
(三)构成商标侵权
十、湖北省刮码案件
(一)构成商标权侵权、构成不正当竞争
十一、湖南省刮码案件
(一)构成不正当竞争
十二、广东省刮码案件
(一)不构成商标权侵权、构成不正当竞争
(二)不构成商标权侵权
十三、四川省刮码案件
(一)构成不正当竞争
(二)构成商标侵权
十四、陕西省刮码案件
(一)不构成商标侵权、不构成不正当竞争
(二)构成不正当竞争
十五、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一)构成商标侵权
一、浙江省刮码案件
(一)不构成商标侵权、不构成不正当竞争案件情况
(2023)浙11民终127号 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州某化妆品有限公司等与黄某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
法院观点:二维码和生产批号部分信息是否被刮除,与案涉产品是否为正品之间没有直接关系,原告未提供被诉产品为非正品的其他证据,而被告提供了聊天记录等予以证明商品来源合法,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不构成商标侵权。
经营者不负有维护其他经营者商业模式的义务,目前证据无法证实被告系刮码的行为人,同时被告在销售案涉产品时对产品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说明,给予了购买者选择权。虽然被诉侵权产品二维码和生产批号部分信息被刮除,但案涉产品来源信息清晰可见,其他如生产日期、保质期、成分等化妆品类产品的必要信息,消费者亦可通过外包装上的标注获取,不构成不正当竞争。
(2023)浙0281民初19号 余姚市人民法院 宁波艾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孟新娣案
法院观点:被告从原告处购得的正品是否包含硬盒包装,以及其对散装刷头的收纳行为是否属于重新包装。原告未举证证明其对销售代理商发出的商品均存在包装盒,且从常理推断,包装精美的商品通常比散装商品售价更高,刻意去除原有精美包装而销售散装商品的行为均有悖于基本商业常识,故本院认定第三人从原告处购得的正品存在没有硬盒包装的散装商品。商品详情网页向消费者所传递的信息显然为销售散装商品而非精包装商品,保留了标识有原告权利商标及企业名称的白色包装袋,产品来源信息清晰可见,案涉商标区分商品来源的功能未受影响,不构成商标侵权。(但是存在其他侵害商标权的行为,标注了与该商品毫无关联的“米诗昂”或“piecespcs”,一商品出现两个及以上商业来源)
原告未举证证明其向经销商所售商品均有硬盒包装,本院认定被告及第三人在对原告正品进行二次销售的过程中保持了商品的原有状态,未主动进行刮码销售或拆除包装销售,不构成不正当竞争。
(2021)浙08民初202号 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法院观点:被告以刮码销售的不当方式出售被诉侵权产品,但未实质性改变被诉侵权商品的外观、品质,也未破坏商品的商标标识,虽然刮除了部分溯源码,但并影响商标的识别功能。
经营者在市场竞争过程中不负有维护其他经营者商业模式的义务,原告已经通过销售行为获得了相应收益,作为生产者的利益未受影响。被告的刮码行为不构成不正当竞争,也不构成商标侵权。
(2020)浙民终479号 浙江省高院 玫琳凯公司等诉马某甲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法院观点:被告在销售中并未改变商品的品质,产品来源信息清晰可见,其他如生产日期、保质期、成分等化妆品类产品的必要信息,消费者亦可通过外包装上的标注所获取,不会导致消费者混淆,不构成商标侵权。
关于经营者利益,其作为商品生产者的利益并未受影响;关于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被诉侵权产品系正品,如产品质量出现问题,玫琳凯公司和被告均不能因产品被刮码而免除产品责任;关于诚实信用原则,被告不负有法定或约定义务维护玫琳凯公司的直销商业模式。在网店中销售,并作了较为充分的说明告知消费者所售产品的真实情况,不构成不正当竞争。
(二)不构成商标侵权、构成不正当竞争案件情况
(2023)浙0381民初7830号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XX公司、木XX等侵害商标权纠纷
法院观点:原告公证取证的六个未刮码灵众嵌入式天花灯产品系正品,且经本院当庭核验,未刮码灵众嵌入式天花灯产品与其余已刮码灵众嵌入式天花灯产品在外观上并无区别,本院认定被告销售产品系正品。被告在其淘宝店铺中使用被诉侵权标识,旨在描述产品来源,并未超出商标合理使用范畴,不构成商标侵权。
被告不正当地利用原告多年经营所形成的竞争优势,并未在商品详情页面对刮码行为进行告知,依旧以全新正品形式销售,并从中直接获取收益,该行为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对原告的品牌价值造成贬损,属不正当竞争行为。
案号不明 钱塘区人民法院 某生物技术(杭州)有限公司与杭州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某网络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法院观点:被告在实际销售商品时,仅刮去正品溯源码,商品外包装上依旧保留完整的批号、生产日期、失效日期及条形码,虽然其刮码行为客观上破坏了商品的整体性,但不构成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
被告不正当地利用原告多年经营所形成的竞争优势,并未在商品详情界面对刮码行为进行告知,依旧以全新正品形式销售,并从中直接获取收益,其行为既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又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有损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同时对原告的品牌价值造成贬损,属不正当竞争行为。
(2019)浙0110民初17059号 余杭区人民法院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与绍兴市柯桥区杨汛桥镇胡素娟保健品店、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一审法院观点:本案中,虽然商品出售前外包装盒上的生产批号部分及二维码部分被刮除,但该种改变所导致的差异性和该种信息的缺失,并未达到影响商标指示商品来源功能的程度,涉案刮码行为不会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不构成商标侵权。
被告以低于未刮码商品的进价从完美公司的经销商处购进涉案刮码完美芦荟胶商品,其知晓上述序列码及二维码可用来溯源,可见其对于刮码行为及完美公司和其经销商之间关于品牌管控的约定明知或至少应当知晓。被告销售刮码商品的行为,攫取了其他合法经营者的交易机会,破坏了经销该品牌商品的所有经销商之间的正当竞争秩序,构成不正当竞争。
(2019)浙0110民初6192号 余杭区人民法院 玫琳凯公司与李波、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
法院观点:被告在销售过程中并未实质性改变商品的外观、品质,也未破坏商品本身的商标标识,不会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不构成商标侵权。
被告作为在淘宝店铺中销售该品牌商品的经营者,可见其对于刮码行为及玫琳凯公司和其经销商之间关于品牌管控的约定明知或至少应当知晓。被告销售刮码商品的行为,不正当地获取了较其他合法经营者更多的竞争优势,破坏了经销该品牌商品的所有经销商之间的正当竞争秩序,构成不正当竞争。
(2019)浙0110民初4350号 余杭区人民法院 玫琳凯公司与安徽耀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
法院观点:被告销售过程中并未改变商品的外观、品质,也未破坏商品本身或其吊牌上的商标标识,并未达到影响商标指示商品来源功能的程度,不会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不构成商标侵权。
被告对于玫琳凯公司和其经销商之间关于价格管控的约定明知,但其仍主动将生产批号刮损后予以销售,主观上存在恶意,构成不正当竞争。
二、上海市刮码案件
(一)不构成商标侵权、不构成不正当竞争
(2024)沪0104民初22496号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某某公司与王某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审
法院观点:“刮码销售”行为未破坏商品本身的商标标识,且有部分二维码未作破坏,亦未影响消费者的正常使用,该行为并不会导致涉案商标的识别来源功能受损,不会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不构成商标侵权。
不同商业主体争夺商业机会导致经营者竞争利益受损属于常态,被告并无维护某公经销体系的合同义务,相对方可以依据经销合同要求存在违约行为的经销商承担违约责任,以弥补其损失。且本院已注意到,另案中表明某某公司也已调整采用“暗码”溯源方式来应对“刮码”行为对其商业模式的冲击,故不构成不正当竞争。
(2024)沪0104民初22498号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某某公司与冯某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审
法院观点:该些包装盒上某某公司商标识别功能并未受到损害。且冯某就刮码情况已对消费者作了充分告知,其行为并不会导致涉案商标的识别来源功能受损,不会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不构成商标侵权。
关于经营者利益,某公司已经通过销售商品的方式获取了生产商品的利润。此外,公司也已调整采用“暗码”溯源方式来应对“刮码”行为对其商业模式的冲击。由此表明,通过法律禁止的方式来阻断被诉侵权行为对经营者产生的损害缺乏必要性。关于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所销售的商品系正品,如产品质量出现问题,某某公司和冯某均不能因产品被刮码而免除产品责任。从消费者选择权和知情权的角度,冯某在商品链接规格中已明确告知产品刮码的真实情况,不构成不正当竞争。
(二)构成商标侵权
(2024)沪0104民初10142号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防伪码) 某某公司与周某等侵害商标权纠纷一审
法院观点:因涉案商品防伪码被刮除,无法直接进行防伪验证,而周某不能证明涉案商品系正品,属于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
三、江苏省刮码案件
(一)不构成商标侵权
(2019)苏民终898号 江苏高院 云龙区梦梦羽毛百货商行与东莞市益科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纠纷二审
法院观点:被控侵权人将正品标识码损坏或消除后再进行出售的,如果被控侵权产品与正品一致,亦明确标有正品商标、产品名称、生产厂商等来源信息,撕码仅使得产品的标识码不完整,缺失查询功能,而并未破坏商品本身的商标标识,亦未使得产品的品质统一性受到破坏,则该撕码销售行为并未妨碍商标识别功能与品质保障功能的发挥,不构成商标侵权。
(二)构成商标侵权
苏0391民初7053号 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原告浮美实业(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浮美公司)与被告邵勇侠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
法院观点:该产品有多处被刮去商标、防伪码、商品二维码、商品信息标识,这些所缺失的标识记载了大量表明商品生产者及相应商品品质信息,邵勇侠将上述标识刮去后进行商品销售,导致公众容易产生混淆和误认,构成商标侵权。
(2023)苏07民初522号 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南旻一科技有限公司、海州区岗埠农场某食品商行侵害商标权纠纷民事一审
法院观点:被控侵权商品与正品商品存在明显区别,在岗埠某商行未到庭举证反驳的情况下,本院对该被控侵权商品系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予以认定,构成商标侵权。
(2019)苏03民初569号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东莞市益科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与云龙区梦梦羽毛百货商行、孟佩等侵害商标权纠纷一审
法院观点:被告在销售原告生产的商品时,将产品上的防伪查询码撕掉。割裂了上述注册商标与商品间的对应关系,构成商标侵权。
四、河北省刮码案件
(一)不构成商标侵权、不构成不正当竞争
(2021)冀06知民初79号 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太阳神集团有限公司、高碑店市南环路春春保健食品店等知识产权与竞争纠纷民事一审
法院观点:在销售过程中并未实质性改变商品的外观、品质,也未破坏商品的商标标识,虽然刮除了部分溯源码,但并未达到影响指示商品来源的功能,不构成商标侵权。
经营者在市场竞争过程中不负有维护其他经营者商业模式的义务,被告合法方式获得太阳神公司的商品后,太阳神公司已经通过销售行为获得了相应收益,其作为商品生产者的利益并未受到影响。太阳神公司在商品包装上印刷溯源码系其商业自由,但春春食品店出售刮除溯源码商品的行为不构成不正当竞争。
五、安徽省刮码案件
(一)不构成商标侵权、构成不正当竞争
(案号不明2023年) 滁州市人民法院
法院观点:商品被刮码不影响消费者通过包装上的商标、生产厂家等信息将商品来源指向X公司,故不构成混淆,不构成商标侵权。
“刮码销售”行为虽然不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列举的侵权类型,但可以从被诉行为是否损害了一方竞争利益、经营者间是否具有竞争关系、被诉行为是否正当等方面进行衡量。李某明知条码的溯源功能,产品被刮码后X公司难以查明违约经销商进行追责,其主观难言正当,故被诉侵权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六、福建省刮码案件
(一)不构成商标侵权、构成不正当竞争
(2024)闽0203民初2531号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福建某某茶叶有限公司、厦门市思明区某某茶叶店等不正当竞争纠纷民事一审
法院观点:关于溯源功能的破坏,尚不具有通过外部规制予以救济的必要性。溯源码刮除与否、能否从所购得产品上查询到宣传内容或统一零售价,一般不会对消费者自由决策产生实质影响,未告知刮除溯源码所造成的影响也因此相对有限。相反,此类产品增加了购买选择,市场竞争机制难言因溯源码的刮除而受到破坏。销售此类破坏了溯源功能的产品,尚不具有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予以规制的必要性。
关于防伪核验功能的破坏,对于经营者而言,允许破坏防伪标识的商品进入市场流通,将干扰某某香公司对于仿冒商品的识别和判断,给某某香公司维权造成障碍,造成其经营利益减损。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知情权,影响其自由决策,亦损害了品牌方给予消费者的售后服务体验。产品真伪难以判断或核验难度加大,也势必增加消费者与厂家的沟通成本及维权难度,构成不正当竞争。
(2022)闽0203民初1774号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原告浮美实业(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浮美公司)与被告曾尚仪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
法院观点:产品外包装盒和瓶身上的防伪识别特征均已被刮损,商品的防伪标识是用于将产品与品牌权利方紧密联系起来的信息,去除防伪码最终会导致产品识别性变差,更容易被混淆、误认为假冒产品。造成对经营者的商品溯源、防伪管理体系以及品牌服务体系的破坏,最终影响品牌经营者形象和商誉,损害消费者利益,构成不正当竞争。
七、江西省刮码案件
(一)不构成商标权侵权、构成不正当竞争
(2023)赣09民终1422号 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烟台某商贸公司与雷某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法院观点:案涉商品只是去除了条形识别码及数字码,根据商标权权利用尽原则,不构成对烟台某某公司案涉商标权的侵犯。
雷某以低于未刮码商品的进价购进涉案刮码商品,其知晓数字码、条形识别码可用来溯源,可见其对于刮码行为、烟台某某公司与其经销商之间关于品牌管控的约定应当知晓,但仍然通过销售刮码商品等行为帮助上游经销商掩饰违约行为并从中直接获取利益,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构成不正当竞争。
八、山东省刮码案件
(一)不构成商标侵权、不构成不正当竞争
(2023)鲁07民终7884号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法院观点:一、二审均确认被诉侵权产品系正品,被诉侵权产品本身外包装并未缺失,产品来源信息清晰可见,其他如生产日期、保质期、成分等化妆品类产品的必要信息,消费者亦可通过外包装上的标注获取,商标区分商品来源的功能并未受影响,不会导致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混淆误认,不构成商标侵权。
在其生产销售的产品上设置具有防伪溯源功能的二维码,原告已通过其销售模式获取了商品的相应利润,其作为商品生产者的利益并未受到影响,且被告已对产品的刮码情况向消费者进行了告知,消费者在知晓所购商品为刮码商品的前提下仍然选择购买,系消费者基于其自身偏好所做出的自主选择,不构成不正当竞争。
(二)不构成商标侵权、构成不正当竞争
(2024)鲁13民终7388号 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法院观点:商标最主要的功能在于识别商品来源,一般不指向商品的具体销售者。被控商品除了溯源码有黏贴遮盖、无黑色暗码、黏贴的条形码大小不同外,其他部分包括包装盒、内容物均与正品无异,上诉人使用商标的行为不会产生相关公众对商品来源混淆的后果,没有破坏涉案注册商标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不构成商标侵权。
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具有竞争关系。上诉人认可案涉产品在韩国属于直销模式,权利人设置暗码的目的是为了便于查询商品流通等信息,避免产品再次销售,故上诉人对案涉产品遮挡追溯码、消费期限码等行为,客观上破坏了产品的完整性,主观上有隐藏产品来源、防止厂家追踪的目的,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构成不正当竞争。
(2024)鲁0103民初93号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法院观点:原告未举证证明被诉侵权产品为非正品。被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支付凭证、产品区域代理合同、温某某证言等证据,以及根据被诉侵权产品上标注的生产厂家等信息,可证明被告已提供了涉案产品的合法来源,且对被诉产品为正品进行了举证证明,故不构成商标侵权。
被告认可,在明知涉案商品的销售管控体系中有区域性授权销售限制规定的情况下,仍然破坏商品二维码,妨碍了品牌方对商品的查验、管控功能,破坏了品牌方的商品管控体系。从保护消费者合法利益方面,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存在受损的可能性,会导致消费者对权利人产品质量及信誉产生质疑甚至贬损,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营秩序,构成不正当竞争。
九、河南省刮码案件
(一)不构成商标侵权、不构成不正当竞争
(2025)豫02知民终2号 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
法院观点:原告提交的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销售的产品是非正品,即无法证明被诉产品系侵权产品,故根据商标权一次性用尽原则,他人在购买之后无需经过商标权人许可就可将带有商标的商品再次出售,不够成商标侵权。
从被诉产品销售记录可见,明确备注为刮码拆盒子发货,故客户应知晓难以享受正品应有的全部正规服务,故王某燕的销售行为不会对某化妆品公司案涉商标品牌价值产生影响,不构成不正当竞争。
(二)不构成商标侵权、构成不正当竞争
(2025)豫1621知民初263号 河南省扶沟县人民法院
法院观点:无法认定被告销售的系假冒产品,被告也并未对原告商标进行任何破坏、更改,无法认定被告给原告商标利益造成了损害。被告在商品描述、品牌介绍中进行使用并展示商品图片,用以介绍商品的来源及品牌,系对商品来源、品牌、性能的客观描述,未使相关公众对于商品来源产生混淆,不构成商标侵权。
被告在网页商品介绍中明确“区域限制筹码发货”,其对该产品的销售来源、交易途径等不符合正常交易习惯的情况属于明知或应知,但被告仍然刮除溯源码后对外销售,具有故意或者放任助长他人的违约行为并从中直接获利的意图,攫取了其他合法经营者的交易机会,不正当地获取了较其他合法经营者更多的竞争优势,主观上具有过错,构成不正当竞争。
(2022)豫知民终720号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法院观点:无证据证明原告销售的为假冒商品,应推定涉案商品系正品,不构成商标侵权。
被告并非案涉产品的代理商,也并非直接从厂家进货,但其在淘宝店铺相关网页上却作出了“我们保证从厂家进货”“我们是代理商”等描述,这种描述与客观事实不符,使相关公众误以为原被告之间存在授权代理关系,从而获取不正当的竞争优势,构成不正当竞争,此案因更准确是虚假宣传引发的不正当竞争。
(三)构成商标侵权
(2021)豫01知民初1923号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原告浮美实业(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浮美公司)与被告郑州爱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恩公司)、被告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
法院观点:产品有多处被刮去商标、防伪码、商品二维码、商品信息标识,被告爱恩公司将上述标识刮去后进行商品销售,公众无法通过确认相关信息在商品与商标权人之间建立起特定联系,容易产生混淆和误认,构成商标侵权。
十、湖北省刮码案件
(一)构成商标权侵权、构成不正当竞争
(2024)鄂0902知民初133号 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
法院观点:去码行为既妨碍了商标权利人对商品的流通管理、产品质量追踪,导致商标权人的商誉或者品牌信誉等商标权益受损,也致使消费者对商品的真实来源和销售渠道产生误认或混淆,损害了消费者的商品信息知情权、构成商标侵权。
“刮码销售”行为影响了市场公平竞争,消费者可能因为刮码而无法享受到正常售后服务和质量保证,原告方也可能因为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度降低而产生商誉损失,以及难以实现通过溯源码进行品控监管的目的,故被告“刮码销售”行为亦构成不正当竞争。
十一、湖南省刮码案件
(一)构成不正当竞争
(2022)湘0406知民初34号 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
法院观点:被告所销售的涉案产品虽然确系属于原告的产品,但被告并不是原告的经销商,亦未经授权许可在网络电商平台上销售涉案产品。被告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在涉案产品的销售页面中标注“乐草元洗发水官方旗舰店”“天猫官方旗舰店”等字样,从而使被告获得不正当的竞争优势(笔者备注:虚假宣传引发)。
洗发水外包装盒的二维码用于查验真伪及溯源,被告在其天猫店铺产品详情中对此予以援引,视为知晓二维码的功能,同时妨碍了产品经营管理者对产品质量的追踪管理,损害其向消费者兑现产品质量承诺等合法经营权利,使得消费者就质量问题与品牌方的沟通成本更高,在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上,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存在受损的可能性,构成不正当竞争。
十二、广东省刮码案件
(一)不构成商标权侵权、构成不正当竞争
(2024)粤0117民初6147号 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
法院观点:原告所主张的刮码类型主要有以下三类:其一,刮掉防伪标签;其二,刮掉限期使用日期;其三,刮掉商品条形码。上述三类标识不属于商标法所规定的商标标识,上述标识被刮掉,不影响产品上印有的商标继续发挥商品来源识别功能,不会导致消费者产生混淆误认,不构成商标侵权。
防伪标签系产品生产者、销售者附在产品上的特殊标识,能够发挥查询产品真伪、追踪溯源等功能。被告在明知产品防伪标签、条形码、限期使用日期被刮去的情况下仍然销售,主观上具有隐藏产品信息的目的、客观上破坏了产品的完整性的意图,构成不正当竞争。
(2023)粤1972民初21030号 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
法院观点:涉案产品为正品,虽然伪溯源码被刮除,但该种改变并未影响上述商标指示商品来源功能的程度,消费者也不会因该防伪溯源码的刮除而混淆该产品的提供方,也不会影响消费者对商品本身的使用,不构成商标侵权。
防伪溯源码具有生产方管控经销商销售行为的作用,原告仍其然通过销售刮码商品的行为帮助上游经销商掩饰违约行为,并从中直接获取利益,其行为明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构成不正当竞争。
(二)不构成商标权侵权
(2020)粤0307民初33117号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法院观点:根据商标权权利用尽原则,当商品通过合法途径进入到流通领域后,如果他人再销售等商品再次流转行为并未破坏原有商标功能的发挥,就没有必要被禁止。被诉侵权产品本身外包装未有缺失,产品来源信息清晰可见,其他如生产日期、保质期、成分等必要信息,消费者亦可以通过外包装上的标注所获取。
另外,被告经营的涉案店铺在销售被诉侵权产品时,已经在网店上详细说明了所销售产品的全部信息,明确告知了消费者刮除部分二维码的原因,提示消费者“介意勿拍”,已经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即便二维码被部分刮除,消费者也应当知晓其低于正常价格所购买的商品来自于原告授权的运营方并非其官方渠道,对产品的质量和包装有一定的预期,故被告的行为不会导致原告品牌在消费者心中产生负面影响。
十三、四川省刮码案件
(一)构成不正当竞争
(2024)川0681民初3225号 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法院
法院观点:刮码行为主观上有隐藏产品来源的目的,客观上破坏了产品的整体性、导致关键信息丢失,攫取了其他合法经营者的交易机会。被告并未在商品详情页面对刮码行为进行告知,依旧以全新正品形式销售,并从中直接获取收益,被告也没有以其他有效方式告知消费者,消费者在购买被诉侵权产品时不知晓所购商品为刮码商品,容易误认是原装完好、溯源码防伪信息齐全的获授权正品,亦无从知晓因购买刮码产品而无法享受原装商品所应匹配的产品追溯、质量保障及售后服务,该行为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属不正当竞争行为。
(二)构成商标侵权
(2025)川0117民初3031号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
法院观点:被告刮码销售行为是否构成商标侵权,关键在于侵权产品是否为正品。原告主张侵权事实,应首先由原告举证商品是否为正品。但是,原告在其产品上设置了防伪码用于识别正品,被告明知防伪码的作用,却仍在破坏防伪码后实施销售行为。判断被诉侵权产品是否为正品的举证责任应转移至被告。
被告提交的前述证据无法证明被诉侵权产品是正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因此,被诉侵权产品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权商品,构成商标侵权。
十四、陕西省刮码案件
(一)不构成商标侵权、不构成不正当竞争
(2024)陕10知民终24号 陕西省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
法院观点:被诉产品系正品,该商品虽存在刮码情形,但并未破坏商品商标标识,且被上诉人在销售中对刮码情形已作告知,故不会导致案涉商标的识别功能受损,亦不会导致相关公众混淆误认,不构成商标侵权。
被上诉人的刮码销售行为虽存在不当,妨碍了上诉人商品销售对内管理等事项,但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制的扰乱市场竞争秩序行为,被上诉人亦未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涉案“拼多多”店铺商品宣传中均明确“刮码现货”“刮码发货”,从消费者的选择权和知情权的角度,消费者是在知晓该情况的前提下自主做出购买行为,原告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被告实施了混淆行为、虚假宣传等行为。
(二)构成不正当竞争
(2024)陕0203知民初123号 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人民法院
法院观点:被告对刮码详情在产品页面并未作出说明,且在产品页面注明正品包邮。消费者在购买被诉侵权产品时不知晓其为刮码产品,容易误认其是原装完好xxx授权正品,亦无从知晓因购买的xxx产品,自己无法享受原装商品所应匹配的产品追溯、质量保障及售后服务,会导致消费者对权利人产品质量及信誉产生质疑甚至贬损,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营秩序,构成不正当竞争。
(2024)陕0523知民初267号 陕西省大荔县人民法院
防伪二维码被刮涂,但其在产品详情、价格说明等页面并未作出说明,且涉案产品链接显示有“保正品”字样。消费者在购买被诉侵权产品时不知晓其为刮码产品,容易误认其是原装完好、二维码防伪信息齐全的获授权正品,亦无从知晓因购买的刮码产品,无法享受原装商品所应匹配的产品追溯、质量保障及售后服务,会导致消费者对权利人产品质量及信誉产生质疑甚至贬损,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营秩序,构成不正当竞争。
十五、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一)构成商标侵权
(2024)京73民终968号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法院观点:被诉侵权商品上使用的涉案商标与原告的商标基本一致,由于产品缺乏外包装,瓶身上有刮除数字码的情况,无法确认被告某管理公司销售的商品为原告生产的正品。一般而言,商品上带有的生产批号、数字码等信息,可用于商品防伪、流通环节的产品识别,可以通过上述特定信息确认是否系商标权利人自身商品。在商品识别码完整的情况下,商标权利人可予以品牌及品质管理,若经营者去掉相关识别码进行商品售卖,既表明其有意隐藏商品来源的主观目的,亦在客观上造成商品信息丢失、影响商品来源的识别功能,构成商标侵权。
(2024)京73民终969号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法院观点:被诉侵权商品外包装盒底面的生产批号、侧面的数字码和条形码均被刮除,内部瓶身的数字码被擦除,留有擦痕,无法确认是否是某商贸公司的正品,某医药公司提交淘宝拼多多采购记录用以证明系通过从淘宝拼多多平台代发形式发货,上述证据不能证明被诉侵权产品为正品,构成商标侵权。